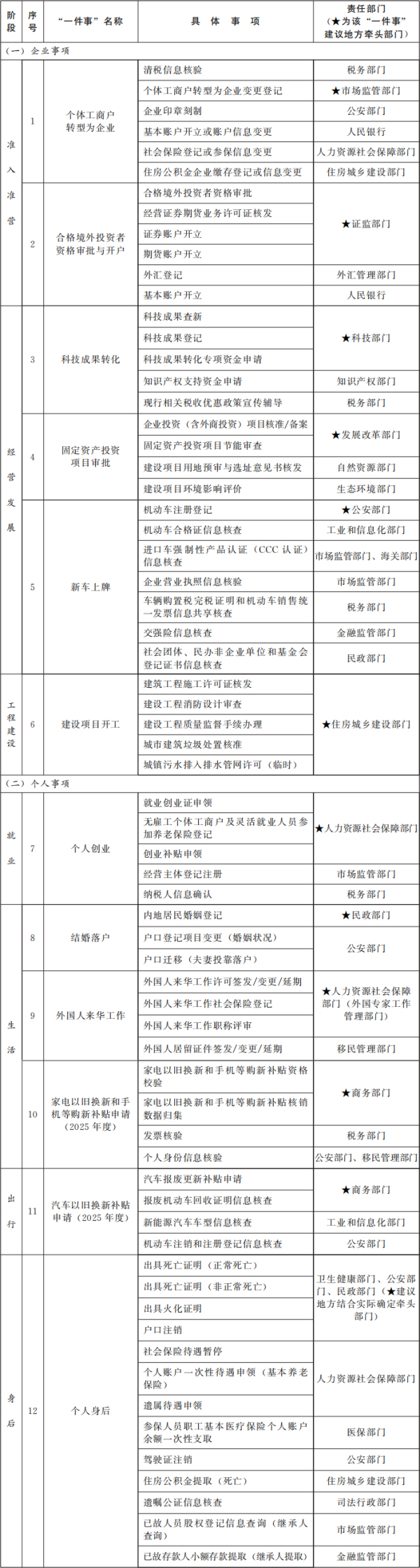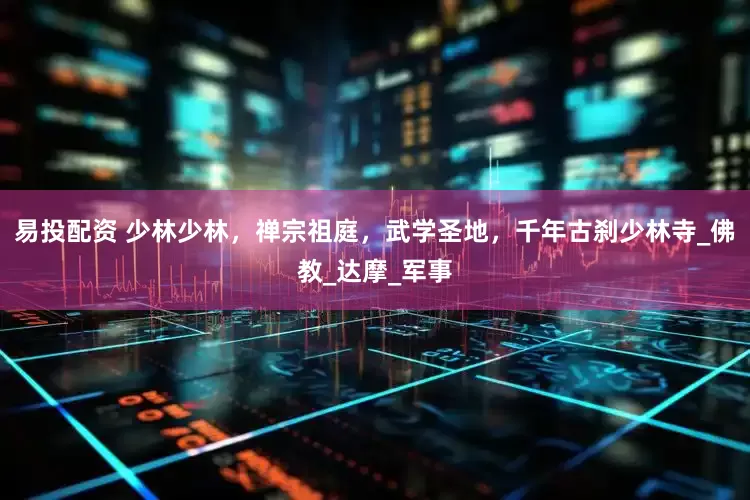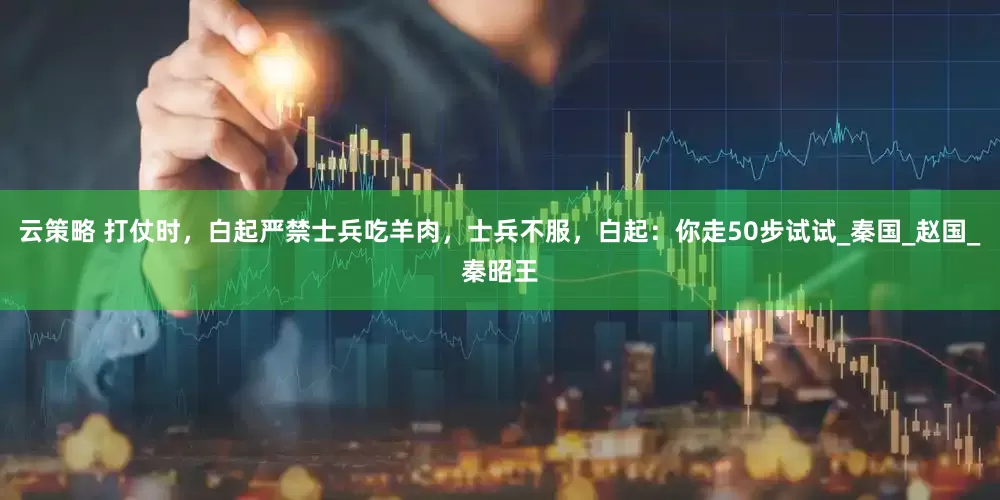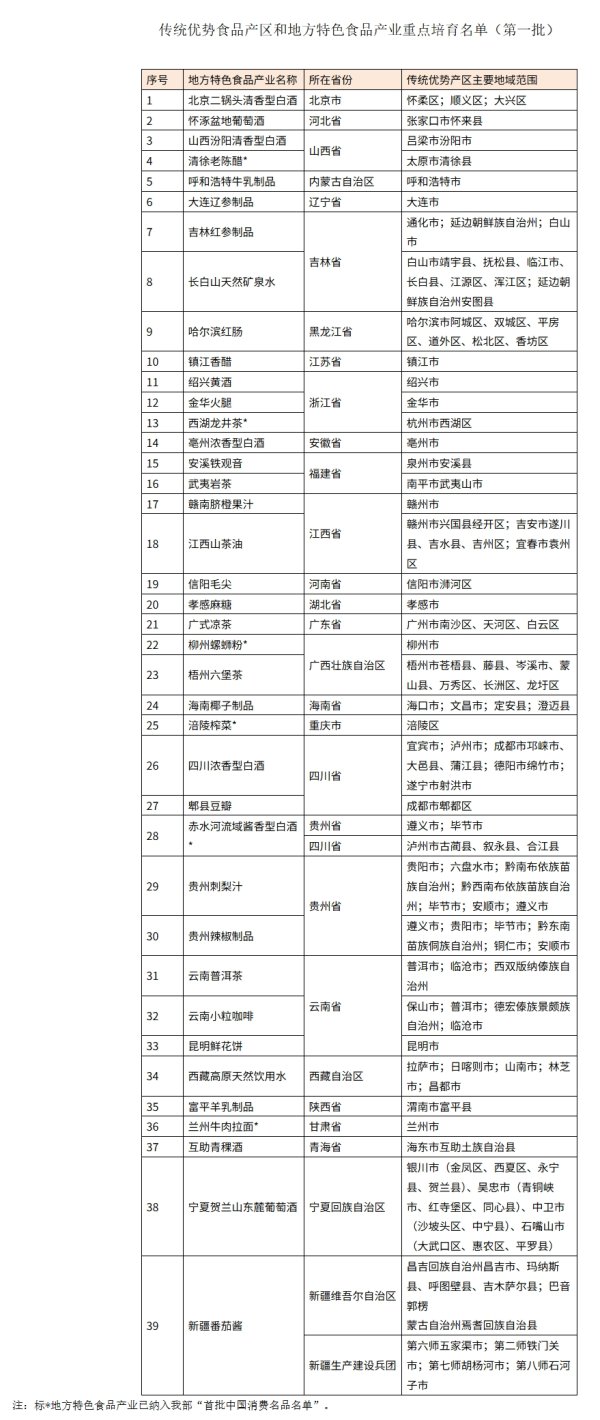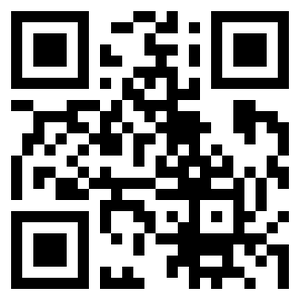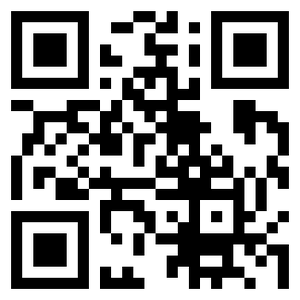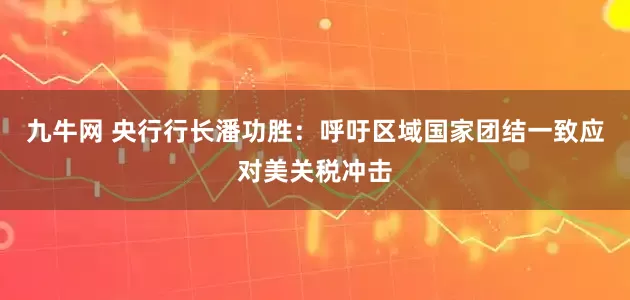“1949年11月的一个傍晚,中南海里灯影摇晃。周恩来轻轻放下茶杯,半带埋怨地笑问:‘老包鑫策略,你这几年到底躲哪儿去了?我可找了你好久。’”一句调侃,瞬间拉近了二十二年的距离,却也揭开了包惠僧最不愿回顾的旧疤。
时针拨回1921年夏日的上海。那间并不宽敞的法租界里弄小楼里,十三位年轻人围坐窄桌,烟火与理想交织——包惠僧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。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书记,他原本打算把汉口码头的工友们都带进新时代。短短两年后,他又领着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,媒体惊呼“长江动了”。那段履历写进档案,也写进同伴们的记忆。

转折来得太快。1927年,蒋汪分裂、白色恐怖骤起。南昌起义出发前,周恩来把一纸介绍信塞进包惠僧手心,叮嘱他养好病就来会合。但当起义部队南下途中溃败的消息传进上海弄堂,包惠僧心里那根弦断了。凑巧,他在报馆谋到一份版面编辑的差事,“先糊口再说”成了最现实的借口。短短半年,他便悄然改换门庭,受聘武汉行营,给何成浚出谋划策。后来职位一路攀升,可在国民党系统里他永远只是“出身复杂”,关键时刻没人真信任他。
抗战爆发后,包惠僧随机关撤至重庆。一次偶遇,周恩来在国共谈判间隙专程跑到内务部寒暄,他却下意识往门帘后躲。多年后回忆起那幕,他苦笑说:“怕牵连,也怕被翻旧账。”这一退,退到1948年——国民政府预算吃紧,人口局裁员,他索性“识相”辞职,举家迁往澳门。赌场灯红酒绿,本想翻本鑫策略,结果输得裤脚发凉。熊十力的劝慰信正是在这种境况中寄到:老友言辞恳切,把时局、友情、责任都摆在纸上,“龙归沧海”四字砸得他彻夜难眠。
1949年10月,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新中国成立。包惠僧终于提笔,给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董必武各写一封长信,既祝贺,也检讨。中央很快回电,邀其北上。有人以为他会犹豫,他却仅用一天就订了船票:“不去,北京会认为我又在观望。”从香港转天津,再乘火车进京,他把身上仅剩的一只行李箱紧紧搂着,好像一松手过去就会彻底散架。

抵京当晚,董必武设宴接风。酒过三巡,董老像训小辈般抬眉:“做了国民党的官,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?”声音不高,却钉在心口。包惠僧放下筷子,低声嗫嚅,连“对不起”都说不完整。几天后,周恩来又在西花厅设小宴,只有寥寥数人。散席时,周总理把他拉到长廊坐下,便有了开头那句追问。包惠僧咽了咽口水,把二十二年的颠沛流离娓娓道来:从上海的踉跄自保,到武汉行营的幕僚生活,再到澳门的萎靡赌博。讲到困窘时他苦笑:“家里十几口要吃饭,我实在没招。”周恩来叹息一句:“生活紧要,但对党,总得有个交代。”
一周后,组织安排他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。课堂上坐着不少旧相识,也有年仅二十的解放军排长。包惠僧被点名作自我剖析,他索性连夜写出三万字《思想总结》。纸面略显啰嗦,却对每一段经历逐一拷问:信念何时动摇?自尊何时战胜责任?读到“我在赌场怒掷筹码之夜,耳边回响的是1921年那句‘开创新天’”,不少同学悄悄红了眼眶。
半年学习结束,包惠僧被分配到内务部,后调国务院参事室。公务不算繁重,他常在午休翻看当年《向导》《民报》的发黄合订本,遇到自己署名的社论就发呆。有人打趣:“老包,这些文章反倒比你现在写的材料锋利。”他呵呵两声,嘴角却掠过一点自嘲:“那时候心里热。”

1979年7月2日,包惠僧病逝于北京医院,终年八十二岁。追悼会上,董必武已经不在人世,周恩来也卧病在床,无法到场。送行的多是后来者,他们站在灵柩前低声议论:党的一大代表只剩两位。有人问:“包老晚年算功臣吗?”一位老干部摆手:“评功过无用,他把欠组织的那一声‘对不起’补上了,就够。”
常有人感慨包惠僧的人生“高开低走”,我更愿意称它为“长线拉锯”。换个角度想,如果1927年那封介绍信没有丢,如果他在重庆不曾躲进门帘,也许今天的史书就是另一种写法。然而历史最无情,也最公允——机会不会因迟到而停留,错过就是错过。幸运的是,他终究赶在落幕前回到舞台,补上了台词,也给后来人留下一面镜子:信念动摇,后果不只是个人命运,更会让一个时代的记录出现空白。对亲历者而言,弥补空白的唯一方式,是转身归队,再晚也不算太晚。
双悦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